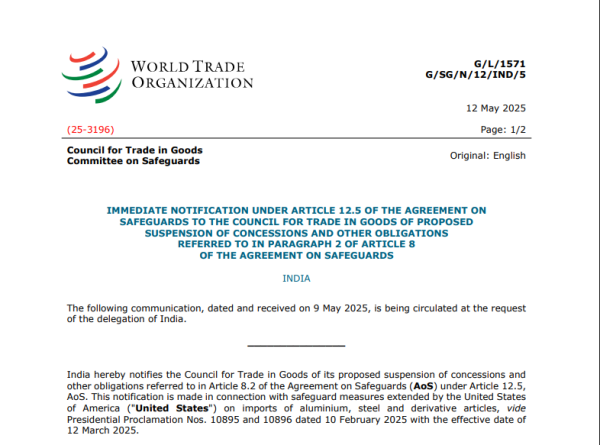“1992年4月15日,老太太,您要坐前排吗?”桃园机场出口处,地勤人员轻声询问。傅涯拄着手杖,抬眼一望,玻璃门外整齐排着十几辆黑色轿车,车灯闪亮配资咨询,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正挥手。她略一点头:“车子多,人更多,事先谁也没告诉我。”一句话,道出惊讶,也透露出三十一年未停的挂念。

机场门口的欢迎阵仗并非官方安排。车队里坐着傅家的儿孙、远房表亲,还有几位黄埔后辈;有人胸前别着小小黄丝带,有人干脆举起“欢迎傅姨”字样的手牌。陈赓的名字,他们都记得,而在台湾更能唤起共鸣的,是那段被无数家庭切开的海峡记忆。
把时间拨回二十世纪初。傅涯出生在绍兴,一家十一口,父亲是典型的绍兴师爷,精明能干;母亲出自苏州书香门第,温婉细致。家境殷实,小女儿却偏爱革命书报,大哥傅森更是早年参加进步活动。1938年春,她追随大哥踏入延安抗大第四期课堂,挥别江南,也断了与父母的常信。
延安的窑洞里,傅涯在文工团排练节目,一位身材颀长、右臂缠绷带的指挥员走进来——陈赓。战争年代的相识,总是快节奏。很快,两人一起上前线、进医院、再上前线。组织曾因傅涯“成分复杂”而犹豫,最终还是批准了婚事。新婚不过数月,陈赓又领命南下,聚少离多成为常态。
1949年解放在即,傅家亲族却随国民党当局东渡。几箱家什、几张银票,外加对大陆亲人的无尽担忧,他们挤进台北城南一间五十来平米的砖楼。黄金被用作军费,市面寥落,父亲不得不带头买所谓“公债”,日子反倒更窘迫。想到回大陆,他跑去排队申请香港过境签,却被港英官方以“危险人物”拒绝。无奈之下,他托人从香港捎信求助。
消息辗转到了广州。傅涯向叶剑英说明情况,香港地下交通站很快汇去一箱港币。本想解燃眉之急,没料到岛内“严禁大陆汇款”的新令正加紧实施。一纸汇款底单,让大嫂、二姐双双入狱;刑期六年、十年,父亲愧疚得夜晚睡不着,逢人便叹:“都是我害的。”
陈赓病逝于1961年。葬礼过后,傅涯常抱着遗像发呆。她相信“台湾不会太远”,却没料到等待如此漫长。转机出现在八十年代。1979年元旦,人大告台湾同胞书发表,两岸气氛松动。1980年夏天,一封贴着旧金山邮戳的蓝色航空信送到家门,信封上隽秀的英文签名让她愣住——最小的妹妹,早年随家人去台湾,后又赴美留学,如今已是美国公民。
信里说,父亲母亲都走了,遗愿是“回到大陆老家,哪怕靠海近一点”。字迹不算娟秀,却字字沉甸甸。七十岁的傅涯戴着老花镜把信读了三遍,才收好,低声道:“得让他们回家。”
1984年5月,妹妹拿着绿色美国护照回到上海。机场大厅,姐妹俩遥遥相望几秒,便击破时空的隔阂,抱在一起。傅涯那年刚中风不久,嘴角仍僵,执意自己走过去。旁人挥手示意让出通道,却无一人出声,静得只能听见行李滑轮的轻响。
安葬父母不容易。台北起灵需要手续,北京安葬要再报批。妹妹先把骨灰带去洛杉矶,再以“转运亲人遗骨”名义报关入境北京。1986年晚春,杭州西子湖畔,傅家兄妹围坐一圈,松木棺中放着两只青花瓷罐。湖面有风,纸钱翻飞,他们没开追悼会,也没鸣礼炮,只是跪在青草上轻声念:“爹娘,我们把您接回来了。”
随后几年,两岸往来的路越来越宽。1992年春节刚过,傅涯正式离休。台湾那边的侄儿写信,说家族想办一次“傅氏团聚”。这次,她不让任何人劝阻:该见的,要见。深知岛内政治审查未停,她主动申请香港过境签,又联系广州军区,请年轻军官随行。事情办得利索,4月,她和妹妹从罗湖口岸出关,经九龙上机。
桃园机场的大阵仗,除亲属外,还混进了几名黄埔军校老学员子女。他们口口声声称“陈公是我父亲的同窗”,执意陪同。出海关不到半小时,车队向市区驶去。前排司机侧头介绍:“阿里山、日月潭、高雄都安排了,傅姨想去哪就去哪。”这种毫无遮挡的自由,在当年并不常见,可见家族和“黄埔情结”的双重面子管用。
两个月里,傅涯跟着弟弟妹妹们跑遍全岛。台北圆山饭店合影,高雄旗津海滩拾贝,日月潭清晨看雾,南投品茶,她不太说话,只是看、只是记。家族聚餐时,给长辈的红包塞满一只手提包,她笑着推回去:“别铺张,留着小辈念书。”
回程那天,家族又排车来送。年纪最小的外甥女偷偷问:“以后还来吗?”傅涯抬手摸了摸孩子脑门,一句“还会见”算是回答。自此以后,傅氏亲人隔年必有人北上探望。探亲证办理流程一次次简化,电话、传真、后来又有电子邮件,他们终于不用再靠暗号、靠口信。

傅涯晚年常坐在北京家中的小院里,翻那本厚厚的合影相册。黑白、彩色、拍立得,比肩的、蹲着的、头发花白的、娃娃脸的,全在里面。有人调侃:“这一册,就是两岸的小缩影。”她点头,不置可否,手指在相片上轻轻摩挲——海峡不止天堑,也能成为家门口那条再普通不过的河。
2
港股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